由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法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法理学与部门法哲学”理论研讨会于2007年8月24-25日在上海举行。参加本次会议的有来自全国各高校、研究机构从事法理学与部门法学研究的专家、学者50余人,共收到学术论文40余篇。入会学者围绕着法理学与法哲学的界限、法理学与部门法哲学的关系、部门法哲学的范围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辩论。本次会议反映了我国法学共同体在理论上深入拓展我国法学研究命题的强烈愿望。现将学者们的主要观点介绍作一介绍。
一、关于法理学与法哲学的划分 在我国法学界,长期以来大家都在习以为常地使用法理学、法哲学、法律科学等概念。对这些概念有无区分的必要?如何区分?区分的意义有多大?入会学者在上述问题上分歧颇大。 有学者认为在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创新中,法哲学应是一个重要课题。法哲学是法学和哲学的交叉学科,但侧重为法学的分支学科,可概括为"法学为体,哲学为用",即用哲学的方法去研究法律现象。法哲学的逻辑起点是法的两重性。法的原则、规则、概念等,都具有客观性和主观性两种属性。这就产生了法律的基本矛盾。法律理论和观念来源于法律和法律制度的现实,反过来,先进的法律思想和法律理论又影响到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发展,这就形成了法律自身发展的两对基本矛盾。 有学者认为法哲学与法律哲学不同。二者的区别有以下几点:第一是两者的研究对象不同。法律哲学所研究的基本对象就是、或主要是国家的实在法问题,而法哲学研究的对象却是事物关系的规定性。第二是两者的研究目的不同。法律哲学研究的目的更多地是提供一种有关法律的知识体系。而这种知识体系的基本面向是司法活动,或者扩大一些适用范围,也主要是法律制定后的法律运用领域。法律哲学的主要作用方向是司法和法律的运用。但是,法哲学却不同,在很大程度上讲,法哲学是提供给人们一种关于法律的世界观、方法论、认识论、价值论等等。它的基本作用路向,是国家的立法领域。因为立法必须关注事物的法的关系的规定性。关注人、人类这种存在的属性和尺度,关注社会交往关系的属性和尺度。否则,立法就有可能走向法律实践的反面。第三是两者的研究结果不同。在前面两点的论述中,我们已经可能看出法律哲学的内容应当是什么。法律哲学的内容主要是形成法律规范的知识属性、逻辑范畴、作用原理、运用方法等等。而法哲学正如前面所言,它更多地是对法——事物关系规定性的研究。因此,其是人们关于事物关系规定性、特别是对人和人的交往关系规定性的本体判断、价值判断、认识方法规定等等问题的学问。第四是两者的研究方法不同。法哲学完全可以是思辨的,当然,也可以采用其他方法进行。因为一种思想性的东西总是以思想者所设定的论证的前提性条件作为基础的。他认为法哲学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完全可能因为人们对自己思想体系的前提准备、或者前见的不同而在研究方法上各取所需。但是,法律哲学却不同。法律哲学的研究方法就一种,那便是规范分析方法。他认为,规范分析方法的基础是根据法律、以及在法律所规范下的社会事实进行研究。也就是说,在法律哲学的视界里,法律自身就规范了研究者的研究方法。法学者是以法律为其幅度和标尺进行法学研究的。规范研究方法是其最重要的研究方法。 有学者认为可以将部门法学称为具体的法律科学,而将法理学称为一般的法律科学。对于法律科学与法律哲学,如果从所取素材的角度讲,法律科学是以实证主义的材料作为其研究的素材;而法律哲学则是以实证材料背后的一般原理为其研究的素材。而如果从法律科学与法律哲学取材的不同而产生的结果来看,法律科学产生的结果是要寻求确定的法律知识;而法律哲学产生的结果却是要寻求正当的法律思想。法律科学是寻求具体问题的答案;而法律哲学是寻求解决具体问题的思想、方法等一些问题。
但也有学者认为法哲学与法理学在历史上并没有明显的区别。哲学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法学。到底法哲学在何种程度上是一门学科,这时值得深思的问题。而哲学是有自己独特特点的学科,它是在经验基础上进行反思的学问,是与其他学科不同的方法论。应用哲学借助的是哲学的基本知识,这样作为一门学科才有意义。至于为什么我们要提出法理学或法哲学的问题以及这种合理性是源于哪里,这是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 二、关于部门法哲学的基本问题 部门法哲学是十多年来法学界在法理学家和部门法学家们的共同推动下,正在迅速崛起的一个新兴研究领域。它以其自身相对独立的知识形态和广阔的发展前景日益引起学者们的兴趣和关注。我国的部门法哲学研究毕竟才算刚刚起步,它有一系列基本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亟待深入地探讨和解决,因此我们又不可盲目乐观和估计过高,而应保持更多的学术清醒和理性自觉。 1.关于“部门法哲学”的发展态势 第一、从理论层面上讲,任何一个学理问题的研究都离不开基本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并且准确的事实判断构成本体论分析和价值论分析的客观基础和必要前提。第二、从实际层面上讲,目前我国法学界对“部门法哲学”发展态势的认识还很不够。 2.关于“部门法哲学”的存在价值 从法理学或法哲学自身的角度看,部门法哲学是以法理学和法哲学向纵深发展以解决其理论贯通性和理论指导力不足的必然需要。而从部门应用法学自身的角度看,它是部门应用法学摆脱其浅层次徘徊进而朝着学理化、哲理化方向提升与发展的必然需要。若从理论法学和应用法学的整体角度看,它是打通理论法学与部门应用法学的隔绝状态、形成二者良性互动机制的必然需要。 3.关于“部门法哲学”的学科属性 有学者指出我们只能有条件地、相对地将其归属于某一学科,而绝不宜断然地判定它就只能是属于某一学科;与其做出某种断然性的归属,莫不如承认它的“双边性”存在。 四、关于“部门法哲学”的名称称谓 从目前学者们所已经使用的情况来看,大体上有以下几种名称或类似于名称的表述被使用:1、“部门法学的哲理化”(或“部门法学的学理化”)。2、“部门法哲学”;3、“应用法哲学”(为西方学者所称,即“applied legal philosophy”); 4、“部门法理学”。而 对于一门学科的存在而言,准确而恰当的名称往往成为其形成或走向成熟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标志。因此,我们需要研究 “部门法哲学”名称称谓的合理性和规范性问题。 三、法理学与部门法哲学的关系 有学者认为法理学与部门法的关系,是很复杂的问题,共有9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思考: 1.部门法为法理学提供了具体的概念与方法。法理学为部门法提供了方法论。 2.法哲学提供问题,包括制度发展中的难题,立法的难题、司法的难题。法理学为部门法提供一种法律政策学。 3.部门法为法理学价值的阐释提供社会价值冲突的个案。 4.从广度和深度来看,各个部门法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抽象的理论。法理学存在于部门法的各个领域,当部门法的理论深化到一定程度时,就形成了法理学。 5.若没有形而下的制度实践,就没有形而上的理论支撑。反之也成立。 6.从知识生产的主体,即各位学者来看,有建树的学者几乎都是部门法的学者。而法理学中的实证主义学者,他们都是专攻某一部门法领域。 7.从法制发展的初级阶段来看,部门法的发展会受到一定限制,要把法理学的引导作用体现出来。 8.法制的成熟期,意味着部门法从立法中心主义过渡到司法中心主义。 9.不同的部门法对法理学的依赖程度是不同的。比如说民法、刑法对法理学的依赖就较少,但行政法、宪法却对法理学的依赖就较大。 有学者认为法理学应当对部门法学起理论指导和启迪作用。但不能过分的强调。他认为法理学与部门法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法理学不是部门法学之上的法学,其源于部门法之中,超乎部门法之外,但不是超乎部门法之上。法理学可以对部门法学的某些“根本难题” 提供一些基本的理论支持,但是,它并不能包医百病,其诊断与解释能力是有限的。法理学、特别是五花八门的各法学学派的法哲学思想与理论,像康德、黑格尔那样极其抽象思辨的法哲学,并非为部门法学而生,自有其天马行空、孤芳自赏的独家领地。法理学或法哲学也是一个独立的法学部门,是与部门法学并存的,有其不同的学术分工。最后,他着重强调了,我国的法理学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所担负的特殊的职责和使命,主要表现在:第 一,法理学有为部门法学披荆斩棘、避风挡雨的作用;第二,解放思想,进行法学启蒙;第三,树立法的根本价值观和选择标准;第四,法学思维方法的渗透。 有学者认为法理学与部门法两者都是模糊的概念,对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只能从总体上进行区别与把握。如果二者的概念、范围与相互间的关系非常清晰、明了,那么我们的理论研究也就停滞了。不再有“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理论研究的光明前景。部门法对法理学理论体系的形成,起着理论与实践渊源的作用。因此,法理学的研究人员,应该对部门法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否则,法理学的研究就会很“空”。部门法对法理学确实有非常强大的反作用。我们看西方国家,他们的法理学的研究,非常深入,但都没有忽视部门法的研究。比如英国的边沁,他是法理学家,同时,他又是社会改革的先驱。因此,我认为,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法理学,不过是人间的梦幻。关于法理学与部门法相互之间的作用可以从理论上或静态去分析,也可以从法律运行或动态的角度,去研究法理学对部门法的推动、指引作用。在此,我就从动态也即法律运行的角度去分析,法理学 对部门法的作用,主要有:法理学有助于部门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有助于具体条文的制定、有助于确定部门法的范围等作用。 有学者认为 法理学与部门法哲学的相互关系,多少年来,大家给它们赋予了一个不恰当的定位,总是认为法理学对部门法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这样的定位,陷入了一个误区。因此,中国法理学的研究,一直受到部门法的责难。对此,他认为,法理学是一个独立的学科,它有其自己的知识体系,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法理学与部门法最大的区别是:部门法是单一的以一个部门法体系为依托,而法理学依托于所有的法律制度,视野更广泛。我们一方面,不可把法理学抬到“云端”的高度,另一方面,我们必须肯定法理学有其独立存在的必要与价值。德沃金 说过:“任何法官的意见本身就是法哲学的一个片段,甚至哲学被掩盖,人们只能被引证和一系列事实支配,其情况也是如此,法理学是判决的一般组成部分,亦即任何依法判决的无声开场白。”法理学与部门法之间是有区别的,但相互之间有很多原理是相通的。不要追求学科性质的法理学,应该从实际问题出发,以法理学的问题为视点。他说,当我们有了一个积累的过程以后,自然就能形成一个理论体系。他还提出了一些研究具体制度的法理学,如回避制度。另外,他还提到了案例法理学的设想。任何一个法律问题背后,都有一个原理性的问题,每个判决后面都有一个法哲学。 有学者实证地考察了法理学对部门法的作用。他认为,法理学对部门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技术层面;为什么民法哲学能搞下去,因为它主要专注于关注民法的问题。历来的哲学家的理论研究大都是建立在对民法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的。其次,徐国栋教授认为,法理学对民法是有一定作用的。他论述了民法哲学包括的对象论、平等论、能力论、生死论、生态论、认识论、人性论、价值论等几个主要问题。徐教授还认为,部门法哲学是分层次的,这些层次不是平等的,而是以民法哲学为中心 的。而民法哲学就是部门法哲学的中心和主要学科。西方的大部分法哲学都是民法哲学,这是一个历史性事实。他还认为部门法哲学具有虚实结合、学科渗透,具有问题取向、最后合成等特点。并认为,法理学会给我们部门法的研究有很大的启示意义。 四、关于各部门法哲学的论题与命题 有学者侧着重从宪法的角度阐释了部门法哲学问题,认为:第一,传统上,从法律的宏观角度,采取二分法,分为公法与私法,并把宪法划到公法之中,因此,其严重的后果是在私法领域就排斥宪法。他认为,正确的应该是采取三分法,既公法、私法、根本法。到底哪一种分法更好,这就让我国的学者有很多的事情可做了;第二,政党的领导与执政问题。他提出“依法执政“与”依法领导“要加以区别。他认为要把领导纳入执政概念的范畴。所以,我们应该认真的研究一下“执政”。但我们的法理学与宪法学没有研究好执政这个词的概念。第三,分权与分工问题。童之伟教授认为,我们中国的宪法是分权的宪法,我们中国的法律制度是分权的法律制度,没有什么分工而不分权的体制。第四,司法这个概念的意义。他提到,现今,在检察院与法院之间已经展开了一场是否是“司法机关“的争夺。我国宪法并没有”司法“这个概念,但是,我国的刑法已经使用了“司法“这个词。这是由于受”三权分立“这种学说的影响。我们是被误导而使用了”司法机关“这个词。他认为,应当将”司法“两个字回归到审判,或者是对”司法“这个词重新进行解释。 我国刑法哲学的发展方向应该是,1、基础性。他们认为,中国法哲学必须加强对刑法哲学本体与基础问题的关注,将厘清刑法哲学的研究范围、层次方法和视域等问题作为刑法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探寻刑法哲学在中国刑法研究领域中的功能、价值与作用。2、 现实性,中国刑法哲学必须以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为旨趣,应当关注中国乃至国际刑法发展中的现实性问题。3、批判性,这时中国刑法哲学成熟的标志,中国刑法哲学应该以理性批判为导向,以借鉴性而非移植性吸收为原则。4、广泛性。在未来中国刑法哲学发展的过程中有必要提出刑法哲学的普及性问题。而在当前中国,刑法哲学尚处于未普及的状态,因此,需要在这方面加强。 有学者主从了国际法的人本主义倾向阐释了法哲学思想的变迁对国际法的影响。指出: 第一,个人应和国家一样,被确认为国际法的主体,人权和主权共同构成国际法体系的基点。 第二,国际法的调整对象在扩大,已扩及到包括个人在内的国际社会关注事项,因此,不仅仅是国家间关系,而且为国际社会所关注的国家与个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也要在一定程度上纳入国际法的管辖范围。 第三,国际法的宗旨,不仅仅在于规范国家间的分立和竞争、倡导国家间的共存和共同发展,而且在于促进人类社会整体的自由和福祉。这一价值取向应构成国际法规则效力的实质性渊源之一。 第四,强调人权保护和人类福祉,主张以人为核心,来理解、解释、适用和发展国际法的原则、规则和制度,构建一个以人为导向的国际法体系。 人本主义的主张现在虽没有被国际社会所普遍接受,也尚未成为国际法的主流价值观,在可见的未来,国际法仍将在现行体系下运行,人本主义不可能取代当前的国家间法律的理论框架。但是谁也不能忽视人本主义对现行国际法带来的冲击和影响。在今后一段时间的国际法很可能是由实在法主义和自然法主义共同作用或交错作用下发展,二者在理论上一竞雌雄,共同主宰、指引国际法的发展方向。
(文/齐延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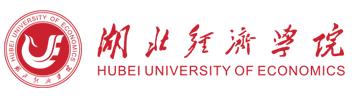
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