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正犯是按分工分类法所确定的一种共犯类型,是共犯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我国刑法虽未使用共同正犯一词,但理论上一般认为数人共同实施犯罪时,犯罪的性质应由实行犯来决定,因此并不否认共同正犯对于正确定罪与量刑的重要意义。
一、共同正犯的概念
“概念乃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限定的专门概念,我们便不能清楚地和理智地思考法律问题。”[1] (P486)而所谓“概念之定义,意为对在什么意义上适用某一特殊用语作出精确的说明”。 [2] (P90)因而理解概念极为重要的一点即在于“在什么意义上”,它表明运用概念的目的、场合不同,其概念对象所界定的外延也不一样,同时概念所涵定的内容也会相应地有区别。共同正犯的概念即是如此。
在德日等国,共同正犯是法定的共犯种类,如《德国刑法》第25条(正犯)规定“自己实施犯罪,或通过他人实施犯罪的,依正犯论处。数人共同实施犯罪的,均依正犯论处(共同正犯)。”《日本刑法》第60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行犯罪的,皆为正犯”。因此,学者们多根据法条的规定来给共同正犯下定义。不过在具体结论上,有的学者将共同正犯理解为一种犯罪形态,有的学者则理解为一种犯罪人。如山中敬一认为:“共同正犯是二人以上共同实行犯罪的情形。”[3] (P782)野村稔则直接根据《日本刑法》第60条前半段的用语,认为“共同正犯是两人以上共同实行犯罪者”。 [4] (P396)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是因为中文的“犯”字本身具有“犯罪人”与“犯罪”这两种含义,所以,从文字上看,将正犯理解为犯罪形态或是犯罪人都是可行的。
在刑法理论界,对刑法研究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存在争议。刑事古典学派认为,刑法研究的重点是行为,应受处罚的是行为。而近代学派则认为应受处罚的不是行为,而是行为人,将研究的重点放在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上。[5] (P22)古典学派与近代学派并因此展开了漫长的学派之争。二战以后,古典学派的客观主义思想占据上风,主观主义的影响力全面减退。但是现代的客观主义已经不再是古典意义上的客观主义,而是吸收了许多主观主义的成分。重视对人的研究,强调刑罚的个别化就是典型的例证。因此,可以说,无论将正犯作为一种“犯罪人”进行研究还是作为一种“犯罪形态”进行研究都有其重要的意义。但是一旦选定一个研究角度,就应当明确研究对象的含义,而不能将一个词交替的在不同意义上使用。这直接关系到刑法用语的准确性与严谨性,也关系到研究的意义。
事实上,如果考虑到正犯一词不过是明治时代日本学者为了翻译西洋学说而借用的中国古代术语的话,那么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在德语中,正犯与正犯者是不同的单词。正犯(T terschaft)指的是犯罪形态,正犯者(T ter)指的则是人。日本学者山中敬一认为“正犯,是指行为人自己充足构成要件要素的场合。换言之,亲自实行刑法分则中记述有‘实行……者’这样的构成要件的人,是正犯者。”[3] (P734)这一定义区分了正犯与正犯者,是科学的,笔者亦采用这种观点,区分正犯与正犯者,而将正犯理解为一种犯罪形态。日本学者所下定义比较简洁,但是同样使用“实行”一词,学者们对其内容的认识却是差别很大。采用形式的客观说、实质的客观说等不同学说,“实行”的内涵与外延都不相同。如果采用形式的客观说,那么只有实施刑法分则所规定的客观构成要件行为的人才属于实行犯。而如果采用实质的客观说,那么虽然没有实施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行为,但只要对犯罪的实现起了重要作用,那么也属于实行犯。显然两者的结论截然相反。作为定义,虽然要求具有高度概括性,语言简洁明了,但同时也要求能够全面揭示出事物的内涵。因此,笔者认为上述定义含义模糊,并不足取。
共同正犯并非我国刑法的法定种类,因而两部刑法都没有共同正犯的立法规定,但鉴于共同正犯概念的重要性,学者们还是没有放弃对共同正犯的研究。如马克昌教授指出:“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实行某一具体犯罪客观要件的行为,在刑法理论上叫共同正犯。”[6] (P525)陈兴良教授强调:“共同正犯是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实施犯罪构成客观方面行为的实行犯。”[7] (P25)在正犯与共犯的区别问题上,我国有学者反对形式的客观说,认为它既有方法论的缺陷,也有难以区分正犯与共犯的实际弊端,从而主张实质的客观说,将实施了可能直接导致危害结果发生的行为人视为正犯。[8] (P345)但笔者并不赞同这种观点,在笔者看来,采用何种学说,必须与本国的法制环境紧密结合。
在德日等国,以分工为标准,将共犯分为正犯、从犯与教唆犯。正犯不仅是定罪的标志,而且在量刑时,也以正犯之刑为标准,来确定教唆犯与从犯的刑罚。正犯被认为是整个共犯体系的中心。这种分类方法比较好的解决了共犯在共同犯罪中的法律性质问题,可以根据形式上是否实施基本构成要件的行为来确定是否是正犯,正犯的确定有了简单明确的标准,从而有利于坚持罪刑法定原则。因此,形式的客观说因为简单明了曾为各国所青睐。但是,由于是否被认定为正犯直接决定了行为人的刑罚轻重,因此正犯概念在事实上又必须具有衡量共犯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大小的功能。这就不可避免的产生了矛盾。如果严格依据形式的客观说,从形式主义的立场来认定正犯,就有可能将在犯罪中起主要作用但并不符合正犯的形式要件的行为排除在正犯之外,而处以较轻的刑罚,这与普通国民的法感情相违背。教唆犯虽处以正犯之刑,但教唆犯之刑既然要以正犯之刑为标准来确定,国民就自然认为正犯才是最恶劣的犯罪人。为此,德日等国不得不放弃形式主义的立场,侧重考虑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将起主要作用的犯罪人认定为正犯,从而使正犯这种按照分工标准所划分的犯罪类型在事实上便成了按照作用分工法所确定的“主犯”。实质的客观说的功能在此,行为支配论的功能也在此。
相比之下,我国在划分共犯时,采用的是混合分类法,即同时采用分工分类与作用分类方法,而以作用分类法为主。这样,我国刑法中的共犯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以分工为标准分为组织犯、正犯、帮助犯、教唆犯;第二类,以作用为标准分为主犯、从犯、胁从犯。由此可见,在我国,正犯与主犯的概念与功能是分开的。正犯只意味着行为人实施了分则所规定的构成要件的实行行为,并不说明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大小。正犯自然可能是主犯,但却无一一对应关系,而教唆犯、帮助犯同样也有可能是主犯。正犯与主犯的分离使正犯概念简单化、正犯功能单一化。这就充分确保了实行行为的定型性,也充分保证了对起主要作用的犯罪人的严惩。
据此,笔者认为,在我国形式的客观说既能充分保证实行行为的定型性,又不会放纵起主要作用的犯罪分子,应当采用这种学说来区别正犯与共犯。综上,笔者认为,共同正犯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实施刑法分则所规定的犯罪构成客观方面行为的犯罪形态。
二、共同正犯的性质
关于共同正犯的性质,即共同正犯是正犯的一种还是共犯的一种,德日刑法作了截然不同的规定。《德国刑法》在第25条“正犯”中规定,“数人共同实施犯罪的,均以正犯论处(共同正犯)”,而日本《刑法》却在第11章“共犯”第60条规定共同正犯“两人以上共同实行犯罪的,都是正犯”。由于两国法律对同样性质的行为在分类上作了不同的处理,引起了学术界对于共同正犯究竟是正犯还是共犯的激烈争论。
一种观点认为,共同正犯始终是正犯的一种,不是共犯。如德国的耶赛克、魏根特等认为,“与间接正犯一样,共同正犯也是正犯的一种形式”。 [9] (P815)日本的木村龟二也认为,“刑法上规定的‘共同正犯’、‘教唆犯’、‘从犯’,虽然说是‘广义的共犯’,但是,正确的理解应当说共同正犯是正犯的共同,即正犯的一种,因为在与正犯相对应的‘共犯’的场合,应当理解为只有教唆犯和从犯这种狭义的共犯”。 [10] (P404)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共同正犯是共犯的一种而不是正犯。例如,日本学者西田典之认为,“如果不把共同正犯理解为共犯,那么就不能很好的说明,单纯正犯集合的形式,为什么要对他人行为的结果承担责任”。 [11] (P26)西原春夫也认为,“共同正犯是共犯,多数学说对共同正犯使用单独正犯的理论加以论述,但不能完全贯彻始终,这是无视共同正犯共犯性的缘故”。 [12] (P315)
我国学者一般是在论及到共同犯罪的形式时才涉及到共同正犯的问题。通说将共同犯罪分为简单的共同犯罪和复杂的共同犯罪。“简单的共同犯罪,在西方刑法中叫共同正犯(即共同实行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实行某一具体犯罪客观要件的行为。”[13] (P173)可见我国通说是将共同正犯作为共犯对待的。但通说也认为“在这种共同犯罪形式中每一共同犯罪人都是实行犯”,这就意味着并不否认共同正犯的正犯性,只是在正犯与共犯的选择中通说更倾向于共犯。林亚刚教授更加明确得指出,共同正犯是共犯,“事物的属性在于其本质特征,共同正犯是正犯的一种还是共犯的一种,关键还在于对这种类型的犯罪的处罚应当依据正犯还是共犯。我们认为,共同正犯虽然具有实行犯的特征,但是,共同正犯的共犯性是其主要方面,对它的认识和处罚的依据,应当是共同犯罪的原理和规定。”[14] (P92)
第三种观点认为,共同正犯可以既是正犯又是共犯。如蔡墩铭认为,“狭义共犯认为共犯只有二种,即教唆与从犯,而共同正犯不与焉,可见共同正犯缺少共犯之性质,所以不能认为共犯”,“倘细予以分析,即知刑法不仅将共同正犯认为共犯,亦将其认为正犯”。他认为共同正犯之共犯性在于“共同正犯所实施之行为,不限于构成要件行为,其可能为一部构成要件行为或为构成要件以外行为,只要基于共同犯罪之意思,皆不失为共同正犯之行为,从而共同正犯之行为实无异于教唆犯或从犯之行为,亦系对於犯罪之参与行为,具有共犯之性质”;共同正犯之正犯性则在于“各个参与者莫不具有正犯意思,亦即认识其所实施之行为与他人之行为结合以後,足以实现构成要件,除此之外,各个参与者对于共同实施之行为,均得予以目的行为支配。易言之,行为之开始,进行或停止,莫不操在各个参与者之手中,分别由各个参与者予以决定”。“刑法第28条所谓皆为正犯,不外指各个参与者独立课以正犯之刑不必考虑对于其他正犯所科之刑如何,此点更足以表示共同正犯所具有之正犯性。”[15] (P325)
关于共同正犯性质的论争,其实际意义在于:如果认为共同正犯是共犯的一种,那么他就应当与狭义的共犯一样,适用同样的处罚根据论。而如果认为共同正犯不是共犯而是正犯,那么两种不同性质的犯罪类型就不可能适用同样的处罚根据论,而必须寻找共同正犯独特的处罚根据论。由此,在共同正犯领域,就形成了鲜明对立的两种学说,即强调共同正犯正犯性的学说与强调共同正犯也是共犯的一种的学说。在前者看来,如果说对教唆帮助适用从属性的原理是妥当的话,那么对共同正犯而言,行为支配论等正犯原理才是正确的。它强调二者的不同。而在后者看来,共同正犯的处罚根据,与教唆帮助一样,都必须在对构成要件的结果(法益侵害)的因果性中来寻找。
笔者认为:第一,不应当用非此即彼的态度来衡量共同正犯。共同正犯是介于正犯与共犯之间的中间类型,既有正犯的属性,也有共犯的属性。单纯将其归为一种类型无法全面的说明其特性。共同正犯的正犯性在于各正犯者所实施的都是基本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行为。这与组织犯、教唆犯、帮助犯等狭义的共犯不同。组织犯、教唆犯、帮助犯所实施的都是总则所规定的修正的构成要件的行为。共同正犯的共犯性表现为,它是复数人的犯罪形态,并不要求每一个行为人都完整的实施分则所规定的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行为,而可以通过分工与协作共同实现一个犯罪,这具有与共犯共通的属性,而与单独正犯显然有异。
第二,单纯将共同正犯归为一种类型难以构筑合理的刑法体系。具体而言,如果将共同正犯视为共犯,那就无法解释为何理论上又将正犯分类为直接正犯、间接正犯与共同正犯,即共同正犯何以又成为正犯的一种。如果将共同正犯归类为正犯,那又无法解释为何要将一些单独正犯情况下不构成犯罪的行为作为共同正犯处理。例如,甲乙共谋抢劫,甲实施实行行为,乙只是站在一边看着被害人。乙的行为若是在单独正犯的情况下显然不构成犯罪,但在二人共谋实施的这种场合,就成立了抢劫罪的共同正犯。这只能根据共同犯罪的原理来加以说明。
第三,应当正确理解法律对共同正犯的不同规定。如前所述,德日等国刑法将共同正犯规定在不同的章节。笔者认为这只是反映法律在作出规定时,更侧重于共同正犯所具有的共犯性与正犯性的哪一个方面,而不意味着法律绝对的否定另一方面属性。以日本《刑法》为例,该国《刑法》在第11章“共犯”中规定共同正犯,日本有学者因此认为共同正犯是共犯,但是仔细分析法条的内容,法条又明确指出两人以上共同实行犯罪的,都是“正犯”。这显然是在明示共同正犯的正犯性。因而,从章节安排上机械的理解法条的态度不可取。日本学者往往过于执著于法条的规定,认为共同正犯是共犯,如“齐藤金作曾经问学生共同正犯是正犯还是共犯,学生们都不知如何回答,齐藤于是说写在共犯一章所以是共犯”。 [11] (P25)但这类学者又深感无法说明共同正犯所具有的正犯性,因此,只能感叹“正犯是正犯还是共犯这样的问题,是最初的问题也是最后的问题(即没有答案的问题)”。 [11] (P27)之所以得出这种结论,就是因为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
就我国刑法而言,应当认为法律更强调共同正犯的共犯性。我国刑法虽未直接规定共同正犯,但共同犯罪一章的内容便可适用于共同正犯。与德日等国不同,我国对共同犯罪的处罚不是以正犯之刑为标准,而是需要进一步分析各个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分别主犯、从犯与胁从犯进行处理。而对主从的区分就意味着对共同犯罪人的比较,这与单独正犯明显不同。
第四,共同正犯既具有正犯性,也具有共犯性,所以在研究共同正犯的处罚根据时,不应当将两者对立起来,绝对的互相排斥,而应当将其内容有机的加以结合,从而完整的解释共同正犯的处罚根据。
第五,台湾学者蔡墩铭虽然正确地说明了共同正犯既是共犯又是正犯的性质,但他对共同正犯正犯性的解释不能为祖国大陆刑法理论所接受。因为蔡先生所采用的是行为支配论的观点,认为“共同正犯所实施之行为,不限于构成要件行为,其可能为一部构成要件行为或为构成要件以外行为,只要基于共同犯罪之意思,皆不失为共同正犯之行为”。如前所述,行为支配论在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影响的扩大有其立法上的深层背景,而在我国法律环境中,应当坚持形式客观说的立场,反对将没有实施犯罪构成客观方面行为的人也认定为正犯。
三、共同正犯的种类
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对共同正犯作不同的分类。
(一)分担的共同正犯与并进的共同正犯
分担的共同正犯是指各行为人基于共同的犯罪故意实施犯罪行为时,在实行行为上具有分工,各行为人的行为相互利用互相补充,形成共同实行行为。分担的共同正犯具有如下特点:
1. 就各个行为人的行为而论,不要求其实施该犯罪构成要件客观方面的全部行为。以抢劫罪为例,在单独正犯的情况下,行为人必须既要实施暴力、胁迫或者其他的手段行为;又要实施夺取财物的目的行为。而二人共同抢劫的,可以由一人实施暴力、胁迫等手段行为,而另一人则专门实施取得财物的目的行为。这与单独正犯有明显的区别。
2. 就各个行为人行为的整体而论,各人的行为相互利用互相补充,必须形成该犯罪客观方面的实行行为。仍以抢劫罪为例,不论各行为人内部如何分工,最终必须既有人实施暴力、胁迫等手段行为,又有人实施取财的目的行为,如此方能形成一个完整的犯罪。否则,如果行为人都只实施暴力行为,那就很难确定行为的性质,即使能够查明主观上抢劫的故意,也无法构成犯罪的既遂。
3. 因所实施犯罪的性质不同,各人的分担行为也有区别。对单行为犯而言,各行为人分担的是一个行为。例如杀人罪是单行为犯,若数人共同实施杀人罪,所分担的都是杀人行为。而对复合行为犯而言,行为人所分担的是数个行为。
并进的共同正犯是指各行为人基于共同的犯罪故意实施犯罪时,各自的行为均充足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要件。这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共同针对同一对象实施犯罪实行行为,例如甲乙同时枪击丙,致丙死亡。二是各行为人分别针对不同对象实行不法侵害,例如甲乙共谋杀害丙丁,甲去杀丙,乙去杀丁。第一种情况,甲乙应共同对丙的死亡承担刑事责任是没有问题的。第二种情况,虽然甲乙各杀一人,但对对方行为的结果都应承担刑事责任。这是共同正犯“部分行为全部责任”的当然结论。
(二)原始的共同正犯与继承的共同正犯
原始的共同正犯,又称预谋的共同正犯,指二人以上在着手实施犯罪实行行为之前,已经就共同实行犯罪形成了意思的联络。这又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各行为人在实施实行行为之前,就已经具有共同实行的故意。另一种是各行为人在着手实施实行行为之际,才产生共同实行的意思联络。有的学者又称后者为偶然的共同正犯。
继承的共同正犯,又称相续的共同正犯,是指对某一个犯罪,先行行为者着手实行后,在行为尚未全部实行终了阶段,与他人(后行行为者)之间产生了共同实施犯罪的意思,此后共同实施犯罪的实行行为的情形。
继承的共同正犯中后行者是否应对介入之前先行者已实施的犯行事实部分也承担共同正犯的责任,学术界对此问题存在争议。笔者认为既不能一概否定后行者的责任,也不能一概肯定后行者的责任。后行者要对先行者之前的行为及其结果承担共同正犯的责任,需要其不仅认识到先行者的行为结果,而且需要先行者行为的效果仍在延续,后行者又有积极的利用意思,将其作为自己的手段加以运用,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才能就整体犯罪成立共同正犯。例如,甲实施暴力压制乙的反抗后,丙介入利用这种状态取得财物的情况。如果丙对此前甲的压制行为有认识,并且有积极利用甲的行为所形成的乙被制服的状态的意思,那么就应当与甲成立抢劫罪的共同正犯。不过如果先行者在实施暴力时致被害人重伤或死亡,后行者介入取得财物,这时后行者所利用的只是因暴力使被害人不能反抗的状态,至于死伤的结果则属于过剩的结果,后行为者只应当与先行为者构成抢劫罪的共同正犯,并不对死亡的结果负责。
(三)实行的共同正犯与共谋的共同正犯
实行的共同正犯,是指二人以上基于共同实行的故意,各行为人都着手实施了犯罪的实行行为。这是共同正犯的典型形态。
共谋的共同正犯,是指两人以上共谋实现一定的犯罪,但实际上只有一部分共谋者实行了该犯罪时,其余的未担当实行行为的共谋者也应当成立共同正犯的情况。共谋共同正犯的概念起源于日本大审院时代的司法判例,此后逐渐为学术界所接受,影响逐渐扩大到韩国、我国台湾地区等,近年来我国也有学者开始主张采用共谋共同正犯这一概念。
笔者认为,日本等国共谋共同正犯概念的提出是刑法理论向现实的妥协与让步。因为在这些国家,以分工为标准将共犯分为正犯、从犯与教唆犯。正犯不仅是定罪的标志,而且在量刑时,也以正犯之刑为标准,来确定教唆犯与从犯的刑罚。正犯被认为是整个共犯体系的中心。因此,是否被认定为正犯直接决定了行为人的刑罚轻重。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原本根据法律的规定,应当以是否实施分则所规定的犯罪构成客观要件的行为为标志来认定是否是正犯,但这会将在犯罪中起主要作用但并不符合正犯的形式要件的行为排除在正犯概念之外,而处以较轻的刑罚,与普通国民的法感情相违背。
在日本这种单一采用分工分类法的法体制下,以上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在坚持“正统”理论与照顾社会实际的两难选择中,司法机关因其打击犯罪的客观需要,不得不优先考虑刑法的打击犯罪功能,因而率先制造出共谋共同正犯的判例。理论界虽对此猛烈抨击,但却无法克服刑法与生俱来的缺陷,因而,有的学者如团藤重光,虽然曾经激烈地反对共谋共同正犯理论,但当他担任最高裁判所法官后又改变了自己的见解,认为“考虑到社会生活的现实,司法部门执著于承认共谋共同正犯,至少在一定限度内,是有其理由的。一般来说,作为法的基础推动法律前进的社会因素同样适用于刑法的领域”。这一席话,正是这种无奈心态的流露。因此,可以认为,共谋共同正犯这种“错误”理论的提出及在日本成为通说的经历,正是日本刑法理论向司法现实妥协与让步的真实写照。
而我国不存在使用共谋共同正犯理论的必要性。如前所述,与日本等国不同,我国在划分共犯时,采用的是混合分类法,即同时采用分工分类与作用分类方法,而以作用分类法为主。因此,在我国,正犯与主犯的概念与功能是分开的。正犯只意味着行为人实施了分则所规定的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实行行为,而并不说明犯罪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大小。正犯自然可能是主犯,但却其与主犯却并非一一对应关系,而教唆犯、帮助犯同样也有可能是主犯。正犯与主犯的分离使正犯概念简单化、正犯功能单一化。这就充分确保了实行行为的定型性,也充分保证了对其主要作用的犯罪人的严惩。
可见,我国刑法理论中的正犯与德日等国刑法上的正犯有着本质的差异。既然组织犯、教唆犯、帮助犯都可能是主犯,而国民对共同犯罪的法感情又集中在“主犯”而非“正犯”之上,这样,在我国引入日本学者都认为的“扩张的正犯概念的”、其实是错误的共谋共同正犯的概念,完全没有必要。
(四)故意的共同正犯与过失的共同正犯
故意的共同正犯,是指各行为人基于共同的实行故意而共同实施犯罪实行行为的情形。这是世界各国都承认的共同正犯类型。
过失的共同正犯,是指二人以上的行为者在共同实施一定的行为时,由于全体成员的不注意导致引起危害结果的发生,对这些人也认定为过失犯的共同正犯的情形。
有的刑事立法明确承认过失的共同正犯。如1928年的《中华民国刑法》第42条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犯罪之行为者,皆为正犯。”第47条则规定:“二人以上于过失罪有共同过失者,皆为过失正犯。”有的刑事立法则明确规定共同犯罪由两人以上共同故意构成,排除过失犯罪成立共同犯罪的可能性。如我国现行《刑法》第25条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二人以上共同过失犯罪。不以共同犯罪论处;应当负刑事责任的,按照他们所犯的罪分别处罚。”但大多数国家的刑法刑法条文既不明确肯定,也不明确否定过失共同正犯与过失共同犯罪,这就使是否应当承认过失犯的共同正犯,成为这些国家刑法理论的一个热点问题。
近几年来,我国学者也对是否应当承认过失的共同犯罪及过失的共同正犯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不过由于我国立法明确否认过失的共同犯罪,因而学者们的观点多是从立法论的角度加以论述。笔者认为虽然主张承认过失的共同正犯的学者所提出的理由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在我国现行立法修改之前,基于罪刑法定原则,是没有办法承认过失的共同正犯这一概念的。
(五)相互的共同正犯与附加的共同正犯
相互的共同正犯,是指各共同行为者的行为单独都无法实现犯罪构成客观方面的结果,必须互相联系互相配合才能实现构成要件结果的情况。附加的共同正犯,是指不同的共同正犯者各自努力充足构成要件的情况。如“20人的共谋者计划实施暗杀,为了提高成功率,20人决定同时发射,结果被害人中弹死亡。调查结果,被害人身中多弹,但仍有未射中的子弹。因此,每一个暗杀者,都有可能没有打中目标”。 [16] (P302)
这种分类方法与我国学者所作的分担的共同正犯与并进的共同正犯的分类有相似之处。其中相互的共同正犯事实上就相当于我国学者所说的分担的共同正犯,但是附加的共同正犯强调的是成功率的提高,因而主要指的是针对同一对象的情况,可以视为并进的共同正犯的一种。但是两类分类方法侧重点不同。
相互的共同正犯与附加的共同正犯是德国学者Herzberg提出来的共同正犯类型。他提出这种共同正犯分类主要是为了批判洛克新的机能的行为支配论。根据洛克新的理论,机能的行为支配就象齿轮一样互相咬合。为了不致失败,不能缺少任何一人。而附加的共同正犯的情况,即使某人不参加,结果也十分可能还是一样。洛克新则反驳,从事前来看,各人的行为具有相互依存关系,因而也存在机能的行为支配。[16] (P302)
日本学者对此问题也展开了研究,山口厚认为,附加的共同正犯的正犯性在于“由于复数行为人的共同行动,减少了失败的风险,提高了行为阶段构成要件实现的危险。因此,共同引起这种被提升的危险性的人,可以视为共同引起了构成要件该当事实。”[17] (P212)但是有的学者则批判说,这与强调“违法性判断的事后判断”的山口说存在矛盾的地方。[17] (P228)
笔者认为,相互的共同正犯之所以成为共同正犯的一种类型,是因为它完全具备共同正犯的成立要件,即各行为人主观上有共同实行的故意,客观上有共同实行的事实。德日学者从提高结果实现的危险性这一角度来论证附加的共同正犯的基础,并不合理。因为即使是多人同时实施一个行为,也不能认为结果实现的可能性就一定增大,而且“提高结果实现的危险性”这一理论无法说明下面所提到的择一的共同正犯的共同正犯性问题。
(六)累积的共同正犯与择一的共同正犯
累积的共同正犯,是指从最初开始各共同行为人都有可能引起构成要件结果的情况。择一的共同正犯,是指从最初开始行为人中就只有一人的行为能引起构成要件结果的情况。如AB两人共同计划杀人,分别埋伏在不同的小道的情况。被害人如果经过A所埋伏的道路,那么A就可以杀害被害人,反之,如果被害人从B埋伏的道路走,则A对B的杀害行为没有发挥共同作用,一般认为A也成为杀人罪的共同正犯。
这是德国学者Rudolphi提出的共同正犯分类类型,他提出这种分类也主要是为了批判洛克新的机能的行为支配论。在Rudolphi看来,前者存在机能的行为支配,而后者不存在。因此机能的行为支配无法说明后者的正犯性。洛克新则反驳说,没有必要对机能的行为支配作狭义的理解。根据事前判断,各人对犯罪计划的成功都发挥了本质的作用。当然,如果埋伏行为被评价为预备的话,那么就欠缺“实行阶段”这一要件,可以否定其共同正犯性。
在日本,择一的共同正犯也是考验强调学者们观点一贯性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不少学者在说明附加的共同正犯时,强调在实施行为阶段,复数人的共同行动,提高了结果实现的危险性。但是在择一的共同正犯的情况下,危险性的提高不是在实行行为阶段,而是在各自埋伏这种预备阶段。在实施杀人行为时,由于只有一人能够引起构成要件的结果发生,便无所谓提升结果实现的危险。鉴于此,日本学者佐伯仁志认为,对择一的共同正犯,不应当从提高构成要件实现的危险性的角度来加以解释,而应当着眼于共同正犯的基础。共同正犯是通过相互间心理的沟通,而共同引起构成要件的结果,由于行为人各自分担不同的行为,从而强化、维持了心理的因果性,这才是择一的共同正犯成为共同正犯的类型之一的原因。 [17] (p236)
笔者认为,择一的共同正犯也完全具备共同正犯的成立要件,即各行为人主观上有共同实行的故意,客观上有共同实行的事实,各行为人在主观上由于对方的存在,强化了自己犯罪的决心,在客观上相互补充利用对方的行为,因此完全应当作为共同正犯进行处理。日本学者佐伯仁志抛弃危险性提高的理论而强调各行为人心理的相互联系的观点有可取之处。
本文原载于《法律科学》2006年第1期
【注释】
【参考文献】
[1][美]博登海默. 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M]. 邓正来.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2][英]艾尔•巴比. 社会研究方法[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
[3][日]山中敬一. 刑法总论Ⅱ[M]. 东京:成文堂,1999.
[4][日]野村稔. 刑法总论[M]. 查理其,何力.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1.
[5]马克昌. 比较刑法原理[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6]马克昌. 犯罪通论[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
[7]陈兴良. 论我国刑法中的共同正犯[J]. 法学研究,1987,(4).
[8]张明楷. 刑法学[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9][德]汉斯•海因里希•耶赛克,托马斯•魏根特. 德国刑法教科书[M]. 徐久生.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10][日]木村龟二. 刑法总论[M]. 东京:有斐阁,1984.
[11][日]川端博,西田典之,日高义博,等. 共同正犯论的课题与展望[J]. 现代刑事法,2001,(8).
[12][日]西原春夫. 犯罪实行行为论[M]. 东京:成文堂,1998.
[13]高铭暄,马克昌. 刑法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
[14]林亚刚. 共同正犯相关问题研究[J]. 法律科学,2000,(2).
[15]蔡墩铭. 刑法精义[M]. 台北: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9.
[16][日]高桥则夫. 共犯体系与共犯理论[M]. 东京:成文堂,1988.
[17][日]山口厚,井田良,佐伯仁志. 理论刑法学的最前线[M]. 东京:岩波书店,2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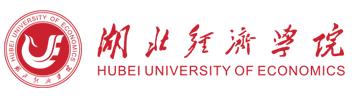
法学院